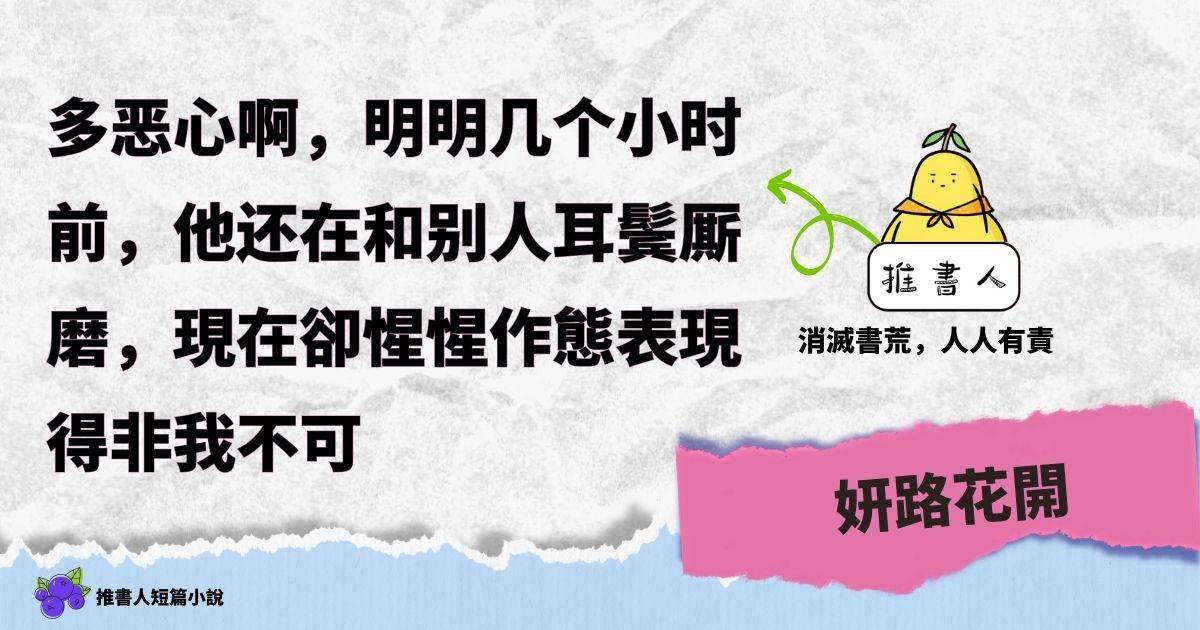《妍路花開》第7章
我笑笑,沒說話。
我確實有這個顧慮。
絕大多數公司的核心資源都不是那張營業執照,而是客戶、產品、渠道和運營,就算宋延知把所有股份都給我,也可以利用資源重組,另起爐灶,到時候股權就一文不值。
拿錢,是對我最好的選擇。
……уž
再次聽到宋延知的消息,是兩個月后。
蔡律師告訴我,他入獄了:
「賭博、欠債不還,因為數額巨大,一審十年起步。」
我有些驚訝,不過后來想想也是。
嘗過錦衣玉食的生活,又怎能忍受重新起家的苦呢?
只不過他選了條最錯誤的路,怪不得別人。
庭審之前,我到看守所去過一次。
宋延知始終低著頭,一言不發。
「你給肖雪買的那套房子追回來了,按照法律屬于婚后財產,理應一人一半。」
「我的那半我拿走了,另一半給你請了個律師。」
我這個人,不喜歡欠別人,做到這樣已經仁至義盡了。
我站起身,和獄警打了個離開的手勢。
離開前,宋延知卻突然喊了聲我的名字:
「妍妍,你還愛我嗎?」
聽得我想笑。
我戴上墨鏡:「外面有配鑰匙的,您配幾把?」
就這樣,我繼續往前走。
路上始終有新的風景、新的冒險。
我把宋氏改名為 Jo,開發了新的品類,放棄高端路線,專注薄利多銷,堅持為貧困地區的女孩售賣低價優質衛生巾,并且成立基金會,免費為貧困家庭的女孩提供技術培訓。
每個產品的包裝上,都會印上這樣一句話:
【I'm not afraid of stroms, for I'm learning how to sail my ship.】
我不害怕風雪,因為我在學習駕駛船帆。
這句話取自 1858 年出版的《小婦人》。
十年前,我第一次讀到這句話,并無感慨。
而今我歷盡千帆,終于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或許人生就是這樣,讀過的閑書、走過的彎路都并非毫無意義。
總有一天,它會在不知名的角落真正體現存在的意義。
不久后,年底市里評選優秀企業家,楊涵陪我去領獎。
她把我送上臺,眼含熱淚:「去吧,再讓我見一次閃閃發光的陳妍。」
我信步上臺,想開口卻語帶凝噎,最終我放棄了講稿,拿起話筒:
「我想對每一個正在經歷苦難的女孩子說:
「我親愛的朋友,你向陽而生,勇敢明亮,生來就該走過山川河海,成為曠野上最自由的風,而非誰人手中的金絲雀。
「可是漫漫長路,難免會遇見一些讓自己身心俱疲的人或事,你被迫沉淪、發怒,希望他們和你一樣,在欲望的苦海里處處不得生。
「但你要明白,人生這條路,怎麼選都會有遺憾,只有及時止損,才能擁有更多。
「你要把那些人狠狠甩在身后,讓你手中的槳,帶你去到人生的任何地方。
「然后你再回頭,就會發現曾經困擾你的,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
「掉在地上的冰淇淋、沒有進步的分數、莫名走散的戀人……
「只要你往前走,一切就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如果愛死去,那就慶祝你活過來。
「還是那句話——
「我獨我,寧作我。」
共勉。
(正文完)
番外
三十四歲的我仍舊沒有結婚,但有了個可愛的女兒。
很漂亮,是個混血,我給她取名叫陳理。
生她的那天,我發了條朋友圈:
【媽媽幫你體驗過了,這個世界還不錯,邀請你來玩一玩。】
楊涵第一個點了贊。
ADVERTISEMENT
五歲時,小姑娘開始出現一些煩惱。
比如,幼兒園里的男生太幼稚了,動不動就想和她結婚。
聽到這個我哭笑不得。
她問我:「媽媽,我將來可以像你一樣不結婚嗎?」
我想了想:「可以。」
她得寸進尺:「那我可以不上學嗎?」
我板起臉:「這個不行。」
小姑娘很失望,隱隱要哭。
我索性放下工作,帶她去外面撿了一天瓶子。
晚上站在燒烤攤前,她拿著賺的四塊五數了又數,發現還不夠買兩根烤腸,只能哭喪著臉,買了串魚豆腐給我:「不然,我還是去上學吧。」
我嘎嘎樂,說:「行。」
最后,我倆在燒烤攤炫了一百多塊。
小理同學很有骨氣,說這頓算她的,先欠著。
回到家,兩道身影在我門口鬼鬼祟祟,我叫保安來處理,最后抓到的人卻是我爸媽。
算了算,我們已經挺多年沒見過了。
我媽伸手就要來抱小理,被我擋住,她也沒說什麼。
我爸倒是開門見山:「你個白眼狼,不回來看看我們就算了,我們也不想管你,但是這回你弟孩子上學,你這做姑姑的,不該表示表示嗎?」
記得和宋延知離婚時,他們也來找過我。
但不是關心我難不難過,而是想知道我能分到多少錢,能給弟弟留多少老婆本。
一瞬間,我竟然有點和肖雪同病相憐的感覺。
月嫂聽見動靜,趕緊把小理抱了進去。
我獨自對陣,一抹戲謔的笑意浮上嘴角:「怎麼,那孩子是我生的?」
見我油鹽不進,我爸沖上來就要打我,又被保安一把按住。
這時候他已經快七十歲,身體大不如前,只能靠撒潑打滾博取同情:
「沒天理了!你當初賣我的房子,現在又要不養我們啊!」
我淡淡道:「那房子本來就是奶奶留給我的。」
一聽這個, 他又開始罵我白眼狼: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