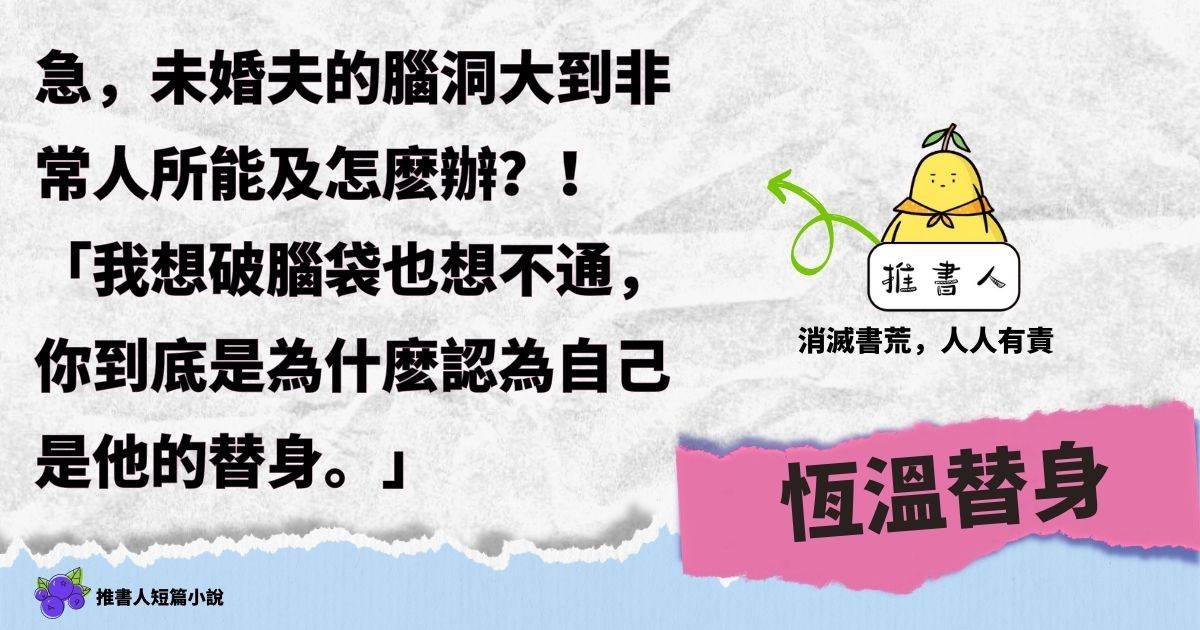《恆溫替身》第3章
」
他停頓了很久,輕笑出聲。
「真會揀我愛聽的說。」
我打開燈,理所當然地點頭。
「當然了,我這麼體貼。」
俞謹倏地起身,不冷不熱地說:
「公司有急事,我先去處理,晚上就不回來了。」
腳步匆匆地擦肩而過,接著就出門進了電梯。
看來真的是很急,身上還穿著睡衣。
我突然有點感動。
這麼著急于工作都要等到我回家再走,真的很關心我。
一大清早,我們前往機場。
俞謹走得飛快,像是生怕誤機。
我不放心地看了一眼手機屏幕——
距離起飛還有兩個小時。
飛機上,我看著身側俞謹空落落的耳垂,掏出口袋里的耳釘。
是昨晚他落在車扶手箱上的。
俞謹盯著手心里的那副耳釘,眼神一瞬間像失落到極點。
「可以不戴嗎?」
我雙眼一亮,還有這等好事。
「家里的那些也不想戴了。」
我:「你說什麼?!」
他躊躇著:「我……」
「真的假的?你要全扔了?」
他抿唇,糾結無比。
我見他實在喜歡,也不忍心他就這麼割舍多年的愛好。
「留著吧,也算是個念想。」
聞言,他攥緊耳釘,聲音沉重:
「你還這麼喜歡?」
我支支吾吾:「嗯……」
關鍵不是我喜歡,而是萬一他又喜歡了呢。
他閉上雙眼:「好。」
再次睜開。
他抬手戴上,手心被堅硬的耳釘刺得通紅。
幾個小時后,飛機降落到 S 城。
臨走前一晚,本來是俞謹處理公務的時間,今天卻十分悠閑。
「你不工作嗎?」
「你那點小心思我還不知道?說吧,想去哪?」
我眼巴巴地看著他,吐出了兩個音節。
Gay 吧。
8
酒吧里,燈紅酒綠。
尋到一處隱蔽的卡座后,我好奇地環顧四周。
俞謹一臉別扭地開口:
「就這麼想來?」
「當然啦,人總是愛追求新鮮事物的。」
他側眸,一字一頓:
「所以,我被那麼多人要聯系方式你也不介意?」
是的,從進門起,俞謹被不下十人搭訕。
恐怕都認為我倆是姐妹。
「委屈一下,讓我再見見世面嘛。」
俞謹聽了,撇撇嘴乖乖坐好。
「乖,我去去就來。」
等我一個小時后回來,傻眼了。
連人帶包全沒了,只留下一個空蕩蕩的酒瓶。
不是,難不成他被人撿走了?
我著急地打開還在包里的耳機定位,發現地點在不遠處的地下潮流街。
尋找了近半個小時,終于在一處出口的樓梯上發現他。
他坐姿端正地抱著我的包,旁邊是一個大袋子。
神情懵懂又認真。
一看就是醉得不太清醒了。
我走近一看,大袋子里全是花花綠綠的耳釘。
得,喝醉了還不忘擱這兒進貨耳釘呢。
我認命般地走過去,把他拉起來。
他眼神從茫然到看見我時變成難過。
「你追求新鮮感,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可是我明明這麼努力,為什麼還能輕易地被取代?」
我懶得分辨一個醉酒之人在說什麼胡言亂語,拉起他就想走。
他一把揮開:「等等。」
說完,他打開袋子,挨個試戴剛買的耳釘。
由于意識昏昏沉沉,他手顫抖得都戴不上。
嘴里還不忘念念叨叨:
「最喜歡哪個,你要什麼我都能有。」
所幸他沒完全醉。
我半攙著他,找代駕回到酒店。уź
進門后,我叮囑他等我一下,松開他準備去倒杯水。
他順勢倒在沙發上,手里卻牢牢地攥住我的手腕。
「你要去找誰?
「他不在這,你就不能看看我嗎?」
ADVERTISEMENT
9
第二天,俞謹匆匆留下一張「有公務」的紙條,先行乘機離開。
還開始夜不歸宿,睡在公司。
我直覺他在躲我,可是平日發消息他卻還是秒回。
不像是對我有意見。
公司辦公時,下屬拿著一份文件,小心翼翼地來找我。
「林總說想親自道歉。」
那日后,我早就打算不再合作,可沒想到他竟然又找上門來。
「問問他時間地點。」
他明顯不是會承認錯誤的性格,找我一定還有別的目的。
只是我想不通,為什麼一個人的變化會這麼大。
從一個光風霽月的少年,變成油膩普信的肥豬。
當然,光風霽月是我想象中的樣子。
他說得沒錯,當年我的確是瞎了。
家庭變故,父親因賭破產。
父母為此吵得不可開交,互揭老底。
我才知道還有同父異母、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甚至只比我小幾歲。
一夜間,我從光鮮亮麗的大小姐變成人人幸災樂禍的對象。
巨大的落差讓我情緒和心理產生嚴重問題。
父親更是接受不了富了半輩子突然變窮,沖動跳樓。
我想去阻攔他,卻被他甩了一巴掌。
「滾,都是你害的。」
可是我做錯了什麼呢,明明我不止一次去澳門勸他回頭。
我被扇倒在地,他扭頭跳了下去。
突然,頭疼欲裂,我昏迷了。
再次醒來就看不見了。
醫生檢查不出來任何病因,只能歸結于心理因素。
我不想承認自己的殘疾,堅持回原學校上課。
林成在那一年確實關照過我。
我從回憶中回過神,想起俞謹和林成合作過。
好像家里還有相關資料。
我發消息給俞謹,問他還有沒有原文件。
「隨你。」
驅車回家,我進入書房。
看完后,我滿臉問號。
合同里的條款絕大多數都偏向了林成公司,就像是白送錢一樣。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