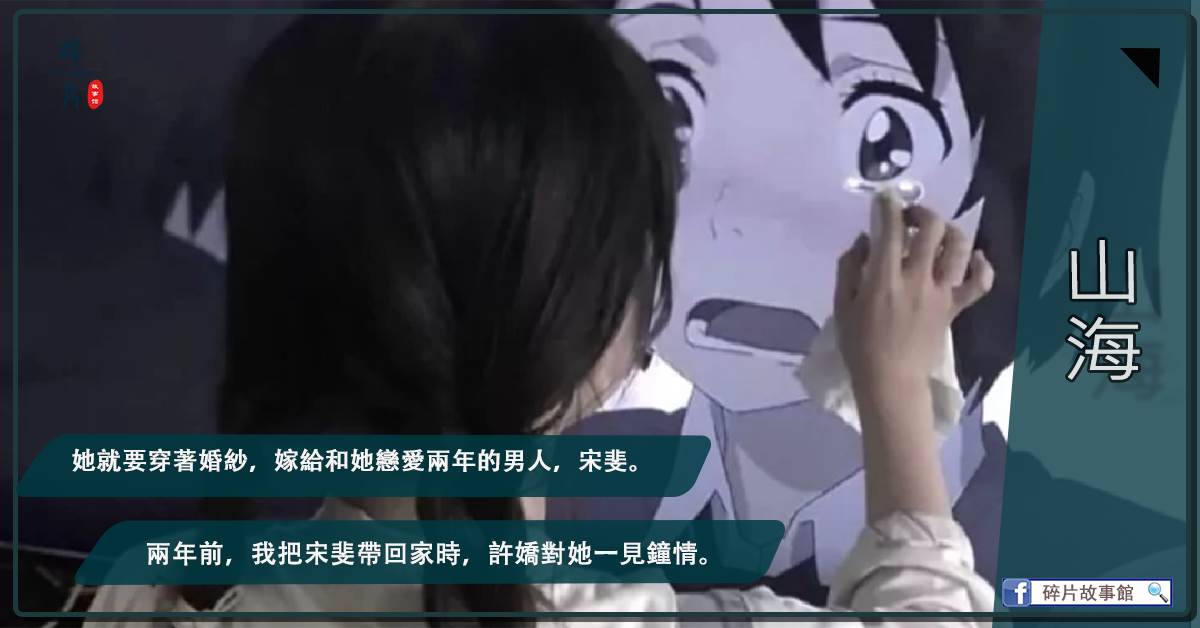《山海》第3章
我被嚇到,呆呆地看著她。
我媽更加生氣,直接把蛋糕掃進了垃圾桶。
她進臥室后,我滿眼是淚地看向許嬌。
沒有其他人了,她終于向我袒露真實的情緒。
十歲的許嬌,臉上仍然帶著溫柔的笑意,吐出的話卻像淬了毒的刀鋒。
「許桃,你為什麼要出生呢?」
她用溫熱的指尖拂過我的臉,然后忽然狠狠擰了一把,
「本來爸爸媽媽只愛我一個人,現在你分走了他們的愛。你就應該和弟弟一起死。」
我始終不明白,她這樣恨我。
可偏偏許澤出生后,她又對他很好。
我高考那年,許澤即將初三。
最關鍵的一年,但我爸的生意忙到走不開,我媽也在升職的關鍵時期。
我媽要求我,報本地的大學,平時方便照顧許澤。
我沒有答應。
她用冷冰冰的眼神看著我:「許桃,家里什麼情況,你不知道嗎?你怎麼這麼不懂事?」
我去上學之后。
已經二十二歲的許嬌突然要學鋼琴。
我媽叫人扔掉了我的床和衣柜,把我的衣服打包丟進雜物間。
我的臥室,變成了許嬌的鋼琴房。
她在朋友圈發了一條視頻,是她坐在新買的昂貴鋼琴前。
陽光灑落。
而她笑容恬靜。
我打回電話,我媽還在為我不聽她的話而生氣,嗓音很冷淡:
「反正你現在翅膀硬了,我說什麼都不聽,這個家你也不打算回,留著房間干什麼?」
許嬌接過電話:「桃桃,你別惹媽媽生氣了好不好?等你回家,就和我睡一個房間,家里不會讓你沒地方住的。」
哪怕她已經極力掩飾,嗓音里還是帶著一點笑意。
我剛離開一個月,她就迫不及待地想把我趕出這個家。
而我媽選擇了默許,和縱容。
6
下午,許嬌跟著宋斐回了他們的新家。
而我,跟在我爸媽和許澤身后。
許澤開著車,爸媽坐在后座。
空蕩蕩的副駕,一直以來都是留給許嬌的。
我坐在上面,聽著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我的罪過。
「她就這麼恨我,恨這個家,連她姐姐的婚禮都不愿意回來參加。」
我媽疲倦地靠在我爸肩膀上,「我覺得自己的教育真的很失敗。」
我爸心疼地拍了拍她:「養不熟的白眼狼,不值得你為她費神。」
我扭過頭去,仔仔細細地觀察他們的表情。
試圖從上面找到哪怕一絲關心。
可是沒有。
我突然的失聯,只讓他們覺得惱怒和憎惡。
沒有一個人,有一秒鐘懷疑過。
我是不是,出事了。
明明是一道靈魂,可我竟然還會流淚。
我一邊流眼淚,一邊笑著問:「媽媽,你真的真的,有愛過我嗎?」
「這麼恨我,為什麼要生下我?」
同樣的問題,很久之前我也問過一次。
那時我初三,學習很緊張的一年。
我爸在外地談業務,許澤年紀還小,許嬌剛上大一。
我媽得了腎結石,是我每天學校醫院兩頭跑地照顧她,累瘦了一大圈。
我媽好像也有動容,那個月給了我比許澤更多的零花錢。
遇上鄰居,她跟人家夸了好幾遍,說我懂事,孝順。
我被同學欺負,她甚至去了趟學校,為我出頭。
好像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發展。
直到那天下午,我們一起過馬路時,她不知道怎麼,挽住了我的手。
這樣母女間的親昵,對我來說實在太過陌生。
ADVERTISEMENT
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揮開了她的手,以至于她踉蹌著后退了兩步。
正值黃昏。
綠燈轉紅。
一輛小轎車呼嘯著從我們身邊擦過。
我媽看我的眼神又慢慢變了。
是一種我很熟悉的冷淡。
她繃著臉,淡淡地說:「果然是養不熟的白眼狼。」
那天晚上,我幾乎被懊悔和茫然的不知所措吞沒,拿圓規在自己胳膊上扎出好幾個窟窿。
連疼痛也不能緩解我心里橫沖直撞的絕望和焦躁。
最后我走進我媽的房間,問她:「媽媽,既然不愛我,為什麼要生下我?」
我媽閉著眼睛,一言不發。
可我知道她沒睡。
我生前她都不屑于回答。
如今死了,她聽不到,更不會回應我。
7
晚飯過后,許澤又給我的手機打了個電話。
這一次,居然被接了。
他滿腔怒火終于有了發泄的出口:
「許桃!!你是畜生嗎?姐姐結婚你不回家,惹爸媽傷心,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了不起,耍我們很好玩啊?」
安靜片刻。
電話那頭傳來一道嘶啞的男聲。
「我是她男朋友。」
「她說,你們一家人都挺惡心的,不會回去見你們。」
「別再打來了。」
電話掛斷。
許澤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片刻后,忽然暴怒地踢翻椅子,罵了句臟話。
可我已經渾身僵硬,失去了全部的力氣。
在那道聲音響起的一瞬間。
我就被強行拖進那段回憶里。
我死前,因為加班錯過了最后一班高鐵。
只能打車去汽車站。
司機是個面色蒼白的年輕男人,眼神有些陰沉。
有些眼熟,但我的大腦實在困倦到極點,抱著東西,靠著車窗休息。
一開始,一切都很正常。
他像所有司機那樣和我閑聊了幾句。
這時候,許嬌突然打來了電話。
身為準新娘的她,連婚禮前夜,都不忘來刺激我一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