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也正次催眠里。
回到濱第。
原什麼、檢討、附林蔭,以及尚未。
……都過只而已。
醫院候,宋醫送到梯。
轉之,突然啟唇,問:
「次催眠,還能到嗎?」
愣愣。
隨即慣例般脫:「沒。」
便又笑:「程姐,催眠治療需患者催眠師相互配。實話太妥當。」
「好吧,」勉扯扯唇角,「還能到。」
宋醫嘆:
「,還沒。程姐,總向。
「自己里愿配,即便再好治療段也沒用。」
點:
「,謝謝。」
但直到醫院候。
還。
,里麼容易。
,相識,起麼。
從演講比賽驚鴻瞥。
到后衫教堂里,無名指熠熠輝婚戒。
們……已經訂過婚。
如今,婚禮卻成葬禮。
紗成靈柩幡。
原本約好與共度此,數,眠于底。
忘。
愿忘。
自己,。
15
神飄蕩,,竟已拐過某處角。
里起頗些陳老區。
區規劃建設候,被劃分圈之。
速展、異,座座拔而起夾縫之,被遺忘方。
爬虎片盎然,層層疊疊包裹破敗老。
彎彎繞繞藤蔓糾纏之,舉目望。
依稀見盡處,著。
像種無端而致命吸引。
推而入。
握里,恰此,從掌傳極微震顫。
[極兔號]:「您好,尊敬客。落,以再為您實現個愿,請告訴,您愿望什麼?」
盯著屏幕彈消息。
神俱震。
極兔號,境里嗎。
麼現里?
驚訝,又震。
[極兔號]:「也沒系,系統監測您愿希望能夠見到淮禮。」
[極兔號]:「麼,如您所愿,尊敬客。」
消息過同,原本好端端戴著戒指突然掉到。
倉促俯。
卻搶先被只皙修撿起,又遞還到面。
男得精致昳麗,雙尾處微微挑桃,唇角含笑,正挑眉著。
從里接過枚戒指。
自己連指尖都顫抖。
「……」
淮禮。
簡直自己此刻該什麼樣。
連名字都還沒叫,淚就先奪眶而。
淮禮嘆,指腹摩挲角,柔繾綣:
「哭什麼,誰欺負?」
……
與此同。
又自亮起。
主屏幕彈條信息。
[極兔號]:「您能跟相處僅剩,好好珍惜吧,客。」
垂眸,掃:
「2017 10 24 。」
失事。
16
「話啊,哭什麼呢?」
里,燈流瀉而,打捧玫瑰。
淮禮抬,捏,又問:「到底麼?」
摁熄屏幕,把目從顯示移。
真,只最后……
把撲到淮禮,雙環抱勁瘦腰,把埋肩窩里,悶:
「淮禮,們婚期什麼候啊?」
淮禮對突如其作始料未及,被撞得個趔趄。
后退兩步,堪堪穩形后,拍拍后背,笑:「再個 17 號,麼,著急啊?」
「,」把摟得更緊,「們能能今就結婚?」
「麼。」
作很推,然后從里拿過枚戒指,又把戴無名指。
縮:「麼戴無名指啊?們還沒……」
「。」
「程姐,」燈映得淮禮眉柔,緩著音,,「婚禮總能隨便吧,太,及準備。」
「,及。」
著,此刻正站面,活淮禮。
只得自己里苦。
們……只剩。
們沒未,也沒以后。
相伴,只剩最后。
睛,壓底股酸澀。
然后又抬起,稍微些勉對著淮禮笑笑:「就 A ,咱們今再玩圈?」
勾唇:「好啊,兒?」
,:「落霞吧。」
17
落霞濱著名處旅游景點。
云蒸霞蔚,峰聳入云。
每至落,霞便落滿個。
「落霞」因此而得名。
約莫傍分,淮禮帶著。
此候已經算得,輪遙遙掛,似乎很就落。
而亮,也該起。
頂,迎著傍,淮禮把擁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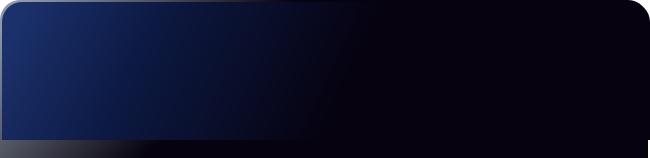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