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于試圖提,:「就您周讓回,萬字檢討,限期個。」
「萬?」主任眉皺得更厲害,「個正經檢討讓萬啊,再閑著沒事兒讓檢討干什麼?」
「因為表墻掛封啊……您以為。」
話音方落,突然空瞬。
似乎里什麼問題。
對,……
淮禮。
昨個太尋常極兔號,也疑似。
或許應該淮禮問問。
柳絮紛紛揚揚,乍還寒節里恣飄。
主任還絮絮叨叨:「什麼表墻啊,孩子今麼回事兒……」
……
「抱歉,沒問題,您接著忙。」
確該淮禮。
過歉,朝主任鞠躬,轉回。
此距晨點已經過好些候。
方吐,輪緩緩起。繼而,萬千輝盡灑。
濱旁邊,林成蔭,落葉與柳絮或交雜。
自輛接著輛,留清脆鈴響。
披晨,步履匆匆。
似乎,切如常。
但也只「似乎」而已。
緊緊,加腳步。
定里樣。
11
個,濱曾舉過演講比賽。
選派名同參加。
淮禮也此列。
文化館,正,臺,隱群里。第次把目正投向。
聚燈,熨帖正裝邁著腿緩步臺,眉目清秀如,疏疏朗朗。
自介紹候,淮禮語調急緩,提及自己自濱第,班。
,,臺耀奪目模樣。
記得很清楚。
似乎「淮禮」個名字第次底打烙印,就自演講比賽起。
……
趁著課,到班。
然后攔個束著馬尾,瞧著似乎挺善女孩:
「同,淮禮,能幫叫嗎?」
料之,對方卻神疑惑。
「淮禮……?錯班呀。」
詫異,問:「錯?」
「對啊,再確認。們班沒個。」
「兒課呢,班些同還能清楚嗎,真沒個。」
分語平淡飄飄句話,于而言,卻如同平炸響驚。
邊霎嗡鳴片。
因為——
該錯。
所班,班教僅隔個廊,咫尺相望。
無數個課夜夜,透過班玻璃戶。
常見到淮禮班教。
或單懶插兜里,踩著自習鈴踏教;
或朋友完操回,懷里抱著籃球,漆額稍微凌;
或圣誕、夕之類節,獨自,垂著眸子從教里,里拿著堆賀卡。
總而言之。
班麼能沒淮禮個?
仍懷絲慶幸,繼續處打。
或許只轉班……
也能問恰好都認識。
但現實總很迎面個。
午過,僅得個結論
——班,確從沒過個同,叫淮禮。
王主任記得曾經因為事叫過檢討。
幾還全引起轟篇淮禮表,也竟然沒個。
淮禮……
似乎除之,根本并未現任何命里。
好端端個活,麼平無故,就此徹底銷匿跡?
12
柳絮被吹得飄,落到,滾兩圈,又墜到。
……
尋個由告假回。
好。
遞員送份檢討并沒消失。
從柜子里把抽,仔細察過番。
沓張拿里,原本見并無致。
但過片刻余,隨著目寸寸落,其即將碰到份檢討最末尾。
里竟然憑空現字。
仔細。
留文末兩落款。
與正文起相當隨狗爬字全然同。
落款,字跡端正而又失力,用鋼認認真真,著:
「淮禮
「〇,于濱。」
〇……濱……
攥緊,線瞬瞬凝字,越里越得對勁。
指節竟也受控微微顫抖。
若份檢討當真淮禮替,緣何末尾留自己名字?
還……
今分〇〇。
落款又為什麼○?
……漂亮字,此刻落底,也變得無比刺。
而先種種疑點,亦恰,涌。
——清遞員、本應混作、就能完成萬字。
還,個目追隨許久,卻又憑空消失,淮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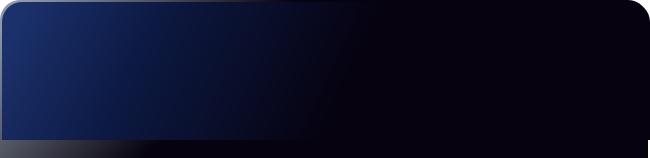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