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劉老師蔣逢森骨按照求,葬。
如果祭奠,臨港就以。
好像切都變,唯到劉老師候,才能從巨變活窺到絲從息。
平劉老師該個嚴厲老師。
到,便滿于忍。
自己如何到臨碼。
還記得里,們共同完成苦肉計,初步取得洪興才信任。
塊兒相對平礁,撲面而咸腥息。
面蒙蒙,些真切。
連燈塔都被掩里。
蔣逢森曾燈塔。
只處暗才能見燈塔。
蔣逢森,很。
隱隱到個朝撲,至沒得及轉過清楚個什麼,就被撲倒礁。
后背傳刺痛。
「嘶。」
「陳老師,麼兒?」
陳澤些尷尬站起,將扶起后,著摸著話。
「以為……?」
連連擺:「沒個,肯定景。」
最終什麼也沒解釋。
們兩沉默著往岸邊,脫套罩肩。
套里陳澤度。
腳步。
「陳老師,也許自作。但還跟清楚,能回應,沒必把浪費。」
陳澤反而如釋負笑:「還以為沒呢,就好。」
沒到麼。
「陳老師,也到,個沒什麼,就座移墓碑而已。
既然事跡,自然也退兩,還名男跟相同事。」指指面,「現就被葬片里,特。」
蔣逢森,沒自己碑,就當墓碑。
原本還愁云慘淡,太陽什麼候,映陳澤。
與將們分割兩個世界。
……
陳澤比象執著。
就侵入活,丹父母也。
至幫組織屆畢業同。
握著,語真誠:「畢業典禮,補。」
很惶恐:「陳老師,什麼都回報。」
度源源斷從掌傳遞到掌,沒系,逼回報,切都順從本而已。
同,認如。
如也撥群擁抱。
些澀回應擁抱。
,因為流逝,缺鏈接而減。
反而如同陳釀酒,歷久彌。
同結束,媽媽打話,跟聊很久。
應該蔣逢森用力保護過方,好好活。
該入個階段,能再渾渾噩噩。
忽然就到首。
故抱劍,斬盡未肯歸。
把自己靈魂留片爛尾,還麼把拉扯到活條湍急流里。
,該讓們如愿。
22
答應陳澤求婚。
切都按部就班著,試婚紗,選酒,選婚慶公司。
陳澤醫院婚檢,病里到個熟悉。
蔣逢森。
兩面蔣逢森。
腳被綁,處處自🩸傷。
沖病后,邊拼命側過躲避,邊用祈求語:「,別。」
見過各種樣子:里耀優秀、洪幫里吊兒郎當混混、起執任務堅定靠。
沒見過個樣子。
個瘦到病態,層層疊疊傷疤。
脆又絕望。
抱抱,告訴很。
至責怪為什麼活著,卻兩都沒。
里只剩激。
謝,讓蔣逢森還活著。
蔣逢森反抗得很激烈,最后護士注射鎮藥物,才睛,入穩眠。
即使,也顰著眉,神痛苦。
病,雙握拳,指甲陷掌之,傳陣陣刺痛,才清。
「對起,陳澤,婚禮還取消吧。」
陳澤著,良久,背過。
「尊決定,若什麼需幫忙方,也以。」
而已經壓抑哭腔,只能遍又遍復著「對起」。
林,麼總邊帶麻煩?
真個糟糕。
張巾被遞到。
「用歉,非招惹,非求段屬于緣分。」
搖:「很好,真個很好很好。錯。」
留病照顧蔣逢森。
起初很抗拒到。
后見堅持,也止反抗。
只遍遍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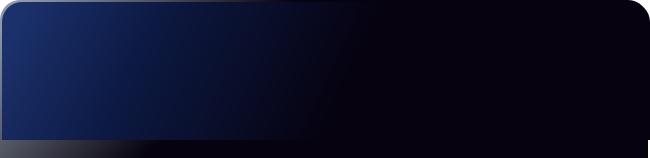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