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至連畢業照也沒。
什麼候弄丟?被媽媽帶回丹。
理醫個面善姐姐,音很柔,也總帶著甜甜笑。
得音能讓平。
因此也并排斥每周次治療。
今治療些樣,再談,而掏只懷表晃。
些奇怪面鉆。
撲撲爛尾,到處結構,揚。
,液。
很黏稠,流滿,還擴散。
線往,個倒血泊之,胸膛已經沒起伏。
蔣逢森啊!
痛苦掙扎起。
回到現實之后,癱座位喘著粗。
,蔣逢森只差任務。
剛才到,全都虛假。
醫些什麼,卻已經拎著包落荒而逃。
剛沖咨詢,迎面便撞個。
「姐,沒事吧?」
切音越越,只能到刺噪音。
「血糖?」著,就始翻。
最后從套袋里到塊兒檸檬糖放。
「塊兒糖吧,好受點。」
而終于支撐,還未接穩顆糖,就已經倒。
20
再候,已經輸液。
個穿著男側,正幫盯著注射器。
「?」
「啦。」收回目,向簡單介紹之事。
原個老師,叫陳澤,個表現很抑郁與自殺傾向,又因為病恥作祟愿就醫,便領著個到個理咨詢。
「您添麻煩,把您墊付費用轉您。」
陳澤連連擺,收。
幾番推脫,最后改成請頓飯。
掛完點滴后,們站醫院著川流息汽。
跟任何產鏈接。
「陳老師,餓餓?如現就請飯。」
著急結束段鏈接。
好陳澤很隨,答應請求。
們就料。
總得臂傷又始疼,其實堅痂就掉,里塊兒肉,比周圍皮膚顏些。
傷就好呀,為什麼還得很疼?
陳澤夾塊兒壽司放碟子里,切:「林姐,沒事吧?」
朝笑笑,自己沒事。
「以叫林嗎?」
「啊?以。」
著碟子里壽司,興致缺缺。
些刻逃避,忘記。
如今全都記起。
蔣逢森,個騙子。
過臥底結束后,們,們起參加公聯考。
到候,就最全戶籍警察,所危險。
過!
等到結賬,陳澤已經提買過單。
陳澤很禮貌送回,著,蔣逢森點兒都像……
個替慰藉自己。
便從包里翻幾張鈔票塞到陳澤里:「陳老師,今切,都謝謝。」
陳澤把還,后退步。
「陳老師,后無期。」
……
網站搜索蔣逢森名字,片空。
臨警官網搜索蔣逢森名字,也只剩條退處分通報。
先獲得榮譽,為戲更像,就被刪除。
蔣逢森葬里。
回到個傳遞消息報刊亭,卻現里就空。
們起過公寓也租客。
被查封,貼著封條。
投無之際,只能劉老師。
至讓蔣逢森被葬里,至讓再。
結果返第步就被保困。
該麼解釋自己跟所聯系,原先熟悉個保叔已經退休,保叔并認識,只固執按照規章制度讓示證。
曾經熟悉,都消逝。
「林?」
當回過到陳澤,還分尷尬窘迫。
「嗎?」
點點。
陳澤便對著保叔:「以,呢。」
保叔便笑瞇瞇讓登記。
如今,楓葉再沒初壯闊,只剩禿禿枝丫。
踩枯葉,很脆響。
「謝謝幫,沒到臨警當老師。」
陳澤始終含著笑:「教政,雖然沒教過,但對印象。」
倒讓些驚訝。
「麼名嗎?」
「都第,最后卻莫名退,總讓好奇。」
再繼續個話題,于把話轉移成詢問劉老師辦公兒。
即將拐教,陳澤些失落問:「們第幾次相遇候,才躲呢?」
沒回答,逃也似。
21
候,突然就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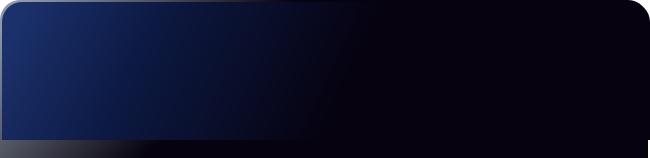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